作為一個熱門概念,我們經常聽到量子計算又有新突破的消息。但很少人清楚,今天的量子計算技術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到底有多少種實現量子計算的方式?本文將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全面梳理,介紹如今各技術流派的發展,以及各科技巨頭的研究情況。
堅持囚禁離子技術的量子計算公司
美國量子計算機初創企業 ionQ 有三位核心成員:馬里蘭大學物理學家 Chris Monroe,杜克大學電氣工程師 Jungsang Kim, 以及原本供職于美國情報部門 IARPA(“高級研究計劃署”)的 David Moehring。其中,前兩位是公司創始人,是研究囚禁離子(trapped ions)的專家。而 David Moehring 是他們雇來的 CEO。
今年九月,這三位還在馬里蘭大學討論量子計算的前景,包括為什么利用囚禁離子能制造出理想的量子計算機––它有完美的再現性(reproductivity),長生命周期,不錯的激光可控性。
這三人有一個共同觀點:量子計算的黃金時代即將到來。它將利用量子力學,為電腦運算帶來指數級得巨幅加速。持同樣觀點的不僅僅有他們。科技巨頭英特爾、微軟、IBM,谷歌都在向量子計算投入千萬美元的研發資金。但是,他們在對不同的量子計算技術下賭注–––沒有人知道,采用哪種量子比特(qubit)能造出有實用價值的量子計算機。
圖表:量子計算五大技術流派
被看做是量子計算領域領頭羊的谷歌,已經做出了選擇:極小的超導電路。谷歌已制造出 9 量子比特的機器,并計劃明年增加至 49 量子比特。這是一個極為關鍵的門檻。學者預計,在 50 量子比特左右,量子計算機就能達到“量子霸權”(quantum supremacy)。這是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學家 John Preskill 發明的名詞,用來指示“量子計算機在一些領域有傳統計算機所不具有的能力”,比如在化學和材料學里模擬分子結構,還有處理密碼學、機器學習的一些問題。
IonQ 團隊并沒有因谷歌的成功而氣餒。Jungsang Kim 說:“我不認為谷歌能在下個月宣布成功研制量子計算機。退一步講,即便他們成功了,游戲也不會結束。” IonQ 堅持使用囚禁離子,它是世界上第一個量子邏輯門背后的技術。那是一個 1995 年完成的項目,Chris Monroe 是參與者之一。使用精確調整的激光脈沖,Monroe 能把離子打入持續數秒的量子態, 這遠超谷歌的量子比特。Jungsang Kim 開發了一個把不同離子群連接到一起的模塊化方案。如該方法奏效,ionQ 就能快速擴大量子比特的規模。但直到現在,他們只成功地把五個量子比特加入到可編程設備中。
Chris Monroe 承認,現在很多人把囚禁離子看作是“害群之馬”,但他堅信,將來人們會蜂擁加入到囚禁離子陣營中。
是否會如此還很難說。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制造量子計算機已經從科學家們的一個遙遠的夢想,變成了科技巨頭們想要立刻實現的目標。ionQ 就是這浪潮中想要分一杯羹的參與者。雖然超導量子比特技術現在是行業領頭羊,專家們認為,現在宣布超導量子比特的勝利,還為時過早。量子信息學非正式院長 Preskill 說:“不同的量子技術在同時發展,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很可能會有驚喜發現,然后帶來量子計算領域的革新。”
量子計算機憑什么超越傳統計算機?
量子比特相比傳統計算機比特更強大,是由于兩個獨特的量子現象:疊加(superposition)和糾纏(entanglement)。量子疊加使量子比特能夠同時具有 0 和 1 的數值,可進行“同步計算”(simultaneous computation)。量子糾纏使分處兩地的兩個量子比特能共享量子態,創造出超疊加效應:每增加一個量子比特,運算性能就翻一倍。比方說,使用五個糾纏量子的算法,能同時進行 25 或者 32 個運算,而傳統計算機必須一個接一個地運算。理論上, 300 個糾纏量子能進行的并行運算數量,比宇宙中的原子還要多。
這種超大規模的并行計算,對于處理日常任務其實沒什么用。沒有人認為量子計算機會顛覆文字處理和 email。但對于需要同時探索無數條路徑的算法,還有對海量數據庫的搜索,量子計算能極大地提高速度。它能被用來尋找新的化學催化劑,對加密數據的海量數字作因子分解(factoring),或許還能模擬黑洞和其他物理現象。
但有一個主要的陷阱––量子疊加和糾纏狀態極度得脆弱,能被環境中的細微擾動所打破,這包括了任何測量它們的嘗試。量子計算機需要被保護起來,與耶魯大學物理學家 Robert Schoelkopf 描述的“汪洋般的混亂”(a sea of classical chaos)隔離開來。
雖然量子計算的理論在 1980 年代就開始出現,直到 1995 年才有了第一次實驗。貝爾實驗室的數學家 Peter Shor,向人們展示量子計算機可以對大量數字快速因子分解––若能實現,這會使現代密碼學的大部分發明過時。Peter Shor 和其他人還展示了,若使用臨近量子比特修正錯誤,讓脆弱的量子比特永遠保持穩定狀態在理論上是可能的。
頓時,物理學家和他們的資助者相信,量子計算機未必會出現一大堆運算錯誤,他們有了充足的理由去嘗試造一臺量子計算機。那時,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者,在 NIST(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工作的 David Wineland 已經開始了對使用激光冷卻離子、并控制他們內在量子態的研究。ionQ 的創始人 Chris Monroe 那時就在 NIST 工作,他與 David Wineland 一起造出了第一個量子力學邏輯門,使用激光控制鈹離子的電子態。有著和 Wineland 研究離子的經驗,Chris Monroe 表示,成為早期量子計算實驗領頭羊的機會,落在了他們手中。
科技巨頭們的量子計算研究進展
超導技術
在全世界,成百上千萬的政府研究資金正流入量子物理學中。隨著研究深入,其他形式的量子比特浮現出來。2010 年開始,囚禁離子技術遭遇了強大的挑戰者: 超導體制成的電流回路。其中,超導體是由接近絕對零度時、攜帶無電阻振蕩電流的金屬物質組成。量子比特的 0 和 1 由不同的電流強度表示。該技術有許多吸引人的優點:1. 電流回路可以被肉眼觀察到。 2. 使用簡單的微波儀器就能控制,不需要對操作要求苛刻的激光。3. 使用傳統計算機芯片制造技術就能生產。 4. 運轉速度非常快。
但是,超導技術有一個致命缺陷:環境噪音。即使是控制設備的噪音,也能在遠遠不足一微秒的瞬間擾亂量子疊加。如今工程技術的優化,已使電路的穩定性提高了近百萬倍,所以量子疊加狀態可以維持數十微秒,但這仍遠遠不如離子。
D-Wave和量子退火
2007 年,加拿大初創公司 D-Wave Systems 宣布,他們使用 16 個超導量子比特成功制成量子計算機。這震驚了世界。但是 D-Wave 的機器并沒有使所有的量子比特發生糾纏,并且不能一個量子比特接著一個量子比特得編程(be programmed qubit by qubit),而是另辟蹊徑,使用了一項名為“量子退火”(quantum annealing)的技術。該技術下,每個量子比特只和臨近的量子比特糾纏并交互,這并沒有建立起一組并行計算,而是一個整體上的、單一的量子狀態。D-Wave 開發者希望把復雜的數學問題映射到該狀態,然后使用量子效應尋找最小值。對于優化問題(比如提高空中交通效率的)來說,這是一項很有潛力的技術。
但批評者們立刻指出:D-Wave 并沒有攻克許多公認的量子計算難題,比如錯誤修正(error correction)。包括谷歌和洛克希德馬丁在內的幾家公司,購買并測試了 D-Wave 的設備,他們初步的共識是,D-Wave 做到了一些能稱之為量子計算的東西,而且,在處理一些特定任務時,他們的設備確實比傳統計算機要快。不論這到底算不算量子計算,D-Wave 把私營企業們震醒了。Chris Monroe 說:“D-Wave 確實打開了人們的眼界。他們讓大家意識到,量子計算機是有市場的,并且有強烈的需求。” 幾年內,各個公司紛紛投入到與他們專業知識相關的各個量子計算領域中去。
英特爾和硅量子點
對量子計算最大的賭注恐怕來自英特爾:2015 年,它宣布將向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的量子技術研究項目 QuTech 投資 5000 萬美元。英特爾專注于硅量子點技術(silicon quantum dots),它經常被稱作“人造原子”。一個量子點量子比特是一塊極小的材料,像原子一樣,它身上電子的量子態可以用 0 或 1 來表示。不同于離子或原子,量子點不需要激光來困住它。
早期的電子點用幾近完美的砷化鎵晶體制作,但研究人員們更傾向于硅,希望能利用半導體產業的巨大產能。QuTech 技術負責人 Leo Kouwenhoven 說:“我認為英特爾屬意于硅,畢竟那是他們最擅長的材料。” 但是基于硅的量子比特研究,大大落后于囚禁離子和超導量子技術。去年,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一只研究團隊才完成兩個量子比特的邏輯門。
微軟和拓撲量子
而微軟的選擇甚至更遙遠:基于非阿貝爾任意子(nonabelian anyons)的拓撲量子比特( topological qubits)。這些根本就不是物體,他們是沿著不同物質邊緣游動的準粒子(quasiparticles)。他們的量子態由不同交叉路線(braiding Paths)來表現。因為交叉路線的形狀導致了量子疊加,他們會受到拓撲保護(topologically protected)而不至于崩潰,這類似于打結的鞋帶不會散開。
這意味著,理論上拓撲量子計算機不需要在錯誤修正上花費那么多量子比特。早在 2005 年,微軟帶領的一支研究團隊,就提出了一種在半導體-超導體混合結構中建造拓撲保護量子比特的方法。微軟已經投資了數個團隊進行嘗試。他們近期的論文,還有貝爾實驗室的一項獨立研究都展示了,關鍵的任意子以電路中電流的模式進行移動的”征兆“。這些科學家已經很接近展示真正的量子比特了。Preskill 說:“我認為在一兩年內,我們就可以看到結果––拓撲量子比特確實存在。“
谷歌的超導量子研究
谷歌這邊,他們雇傭了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的超導量子比特專家 John Martinis 。他研究過 D-Wave 的運行方式和缺陷。在 2014 年,谷歌把整個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研究團隊的全部十幾個人,都給招募了。這之后,John Martinis 團隊宣布,他們已經建成了 9 量子比特的機器,是目前世界上可編程的量子計算機中最大的之一,而且他們正在嘗試擴大規模。為了避免大堆纏繞的電線,他們正在 2D 平面結構上重建該系統。系統會鋪設在一塊晶圓上,所有控制電路都蝕刻在上面。
John Martinis 團隊如今已有 30 名科學家和工程師。七月,他們用了三個超導量子比特來模擬氫分子的基態(ground state)能量,這展示了在模擬簡單的量子系統上,量子計算機可以做到和傳統計算機一樣好。Martinis 表示,這個結果預示了擁有”量子霸權“的計算設備的力量。他還認為,谷歌一年造出 49 量子比特計算機的計劃很趕時間,但或許有可能實現。
ionQ和囚禁離子
與此同時,ionQ 的 Chris Monroe 正在試圖克服囚禁離子帶來的各項挑戰。作為量子比特,它們可以在幾秒鐘內維持穩態,這還多虧了真空裝置和在環境噪音影響下仍能將其穩定的電極。但是,這些隔離措施意味著,量子比特之間的交互變得更難。Monroe 最近把 22 個鐿離子糾纏成一條線形鏈(linear chain),但至今,他還未能控制或查詢所有的離子對,而這是量子計算機必須做到的。
控制組合體的難度,會隨離子數目的增加指數級得升高。所以,加入更多離子是做不到的。 Monroe 認為,解決辦法在于使用模組化的設計,用光導纖維把囚禁離子群連接起來,每個囚禁離子群約有 20 個離子。若用該方案,每個模組中的某特定量子比特都會成為該離子群的中心,從群中其他量子比特那接受信息,并與其他模組分享。這樣,大多數離子會免于外部侵擾。
最近,Monroe 逛了逛他在馬里蘭大學的六個實驗室。在三個較老的實驗室里,電線和真空管路一團團的垂下來。在一張特大桌子上,透鏡和鏡子亂成一堆,使用它們是為了改變激光光束的形狀,并把光束反射入真空室設備的小孔里,那里面就是實驗離子。頭頂上的 HVAC設備們(加熱設備,通風設備,空調)嗡嗡作響。
另外三個新實驗室就十分干凈整潔,甚至空空蕩蕩顯得有些古怪。Rube Goldberg 式的光學實驗桌被整合激光裝置取而代之。Monroe 說:”我們現在用的激光設備只有一個激光球,并且已經開啟。”他焦急得想把 ionQ 的實驗室趕快運作起來,讓高薪聘來的研究人員們正式成為 ionQ 的雇員,以盡快投入到工作中,把他們在馬里蘭大學做的研究完善起來。多虧了和馬里蘭大學不同尋常的協議, ionQ 得到獨家、免費的專利授權。下一年,他會把他的第一個sabbatical 假期用來建立 ionQ。他表示,私營企業對他們量子計算研究的資助,是他事業中最大的一筆錢。
量子計算展望
即便有巨額投資,量子計算在很長時間內,只會是各公司實驗室里的商業秘密。有些大的研究機構,甚至是那些科技巨頭的下屬部門,倒愿意把研究成果在論文和會議上公布出來。他們認為發表最新進展是互利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促使潛在客戶思考量子計算機的應用前景。Monroe 解釋說:“我們都需要一個市場。”與其遮遮掩掩,不如一起把量子計算這塊蛋糕做大。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沒有人對量子計算足夠了解,但每個團隊都選了一個量子比特類型做研究(沒有精力研究多個)。誰知道他們選擇的類型有沒有前途呢?每種方案都需要不斷地優化,擴大規模,最終才能應用于制造量子計算機。無論是制造基于超導體,還是硅的量子比特,都需要極高的連貫性和一致性。對它們冷卻的冷凍裝置也需要改善。囚禁離子需要更快的邏輯門,更緊湊的激光和光纖。拓撲量子比特仍需要被發明出來。簡而言之,要面對的挑戰太多,團隊之間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合作、信息共享,才能加快進度。
未來的量子計算機很可能是一個混合體,由超快的超導體量子比特對算法進行運算,然后把結果扔給更穩定的離子存儲。與此同時,光子在機器的不同部件之間傳遞信息,或者在量子網絡的節點之間。微軟研究員 Krysta Svore 說:“能夠想象,將來不同類型的量子比特會同時存在,并在不同任務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量子計算機是那么新奇古怪,甚至世界的頂級量子物理學家和計算機工程師都不清楚,商業化運營的量子計算機會是什么樣兒。Svore 認為,研究量子計算機應當在行動中摸索。物理學家們只需要試著去造,現有的科技所能達到的最高深的計算機系統,然后面對這過程中出現的難題。 這是一個“制造,學習,重復”的過程。他說:“我們特別喜歡設想,造出了第一臺量子計算機之后,就用它設計第二臺量子計算機。”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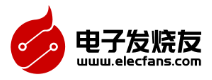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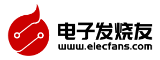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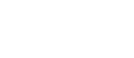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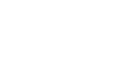





評論